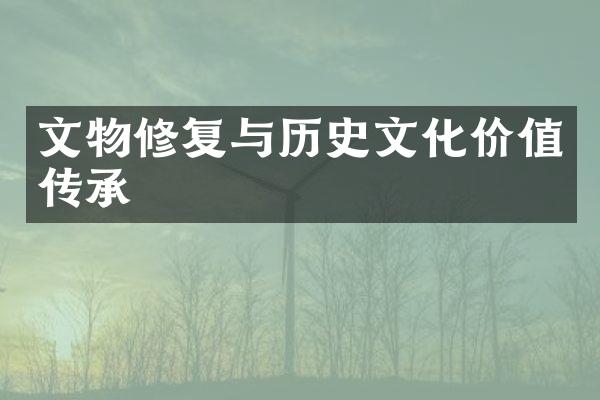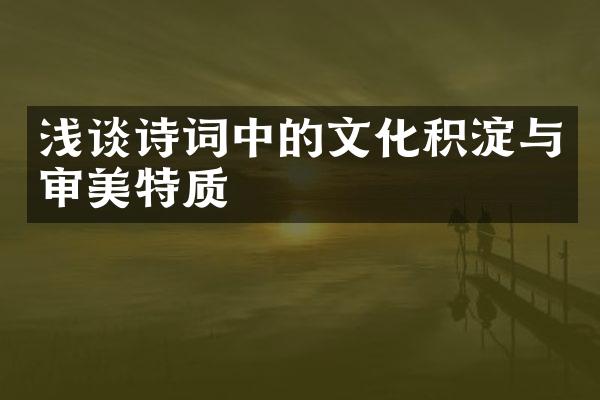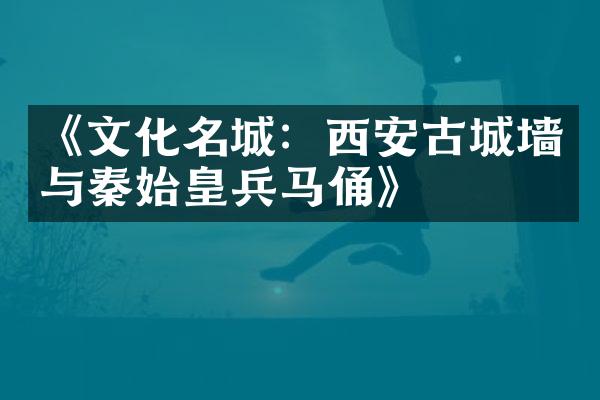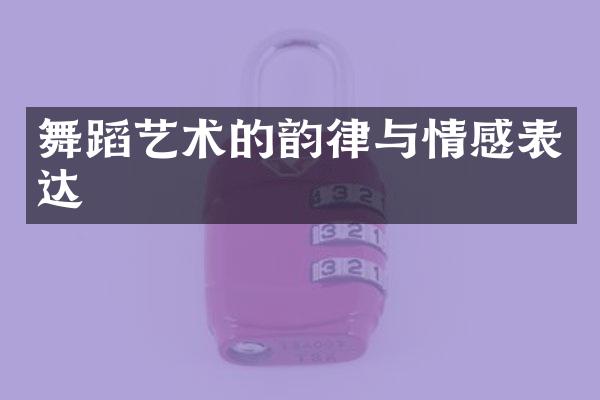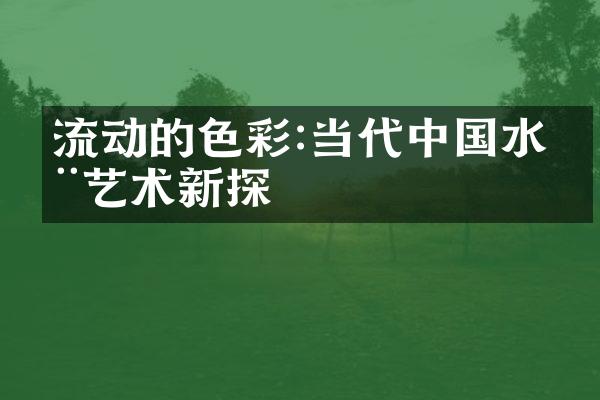诗词韵律中的哲学思考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与宇宙观照,其内涵可从以下多维度展开:

一、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
格律诗平仄相间的声调规则,本质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审美具象化。仄声的短促与平声的延展构成声韵张力,如同《易经》"一阴一阳之谓道"的哲学表达。词牌中"过片"结构的转折设计,暗合老子"反者道之动"的辩证逻辑,展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。
二、天人相应的秩序追求
近体诗严格的押韵范式,折射出古人"律吕调和"的宇宙观。《乐记》"大乐与天地同和"的思想在诗词中具现为:四声对应四方(平上去入配东南西北),韵部呼应节气(如东韵属春、阳韵属夏)。姜夔《白石道人诗说》强调"自然之音节",实为将艺术规律提升至天道法则的高度。
三、有限无限的形上超越
固定词牌格律与自由情感的冲突,催生出"戴着跳舞"的哲学命题。苏轼"不择地皆可出"的创作观,通过格律的有限性抵达意境的无限性,类似禅宗"于相离相"的超越智慧。李清照《词论》主张"别是一家",正是在规范中实现精神自由的审美宣言。
四、时空交融的存在感悟
词体结构中的"换头""摊破"手法,实质是时空意识的艺术重构。温庭筠"玲珑骰子安红豆"的意象叠加,实践了"刹那含永劫"的华严时空观;蒋捷《虞美人·听雨》三叠式结构,以韵律为轴线压缩人生三个阶段,形成柏格森所谓"绵延"的时间哲学具象。
五、虚实相生的认识论启示
"诗眼""词眼"的炼字传统,彰显"以少总多"的思维方法。王安石"春风又绿江南岸"的"绿"字选择,不仅是修辞考量,更是对"道器之辨"的回应——通过具象词汇激活整体意境,暗合王夫之"即体即用"的哲学主张。周邦彦创制新调时的"犯调"手法,本质是打破认知定式的解构实践。
这种韵律哲学的影响超越文学领域: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将词牌结构应用于《数书九章》的算法设计;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更从诗韵规律中提炼出十二平均律的数理模型。可见诗词格律不仅是形式规范,更是中华文明认知世界的元语言,其哲学价值仍有待当代学界的深入开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