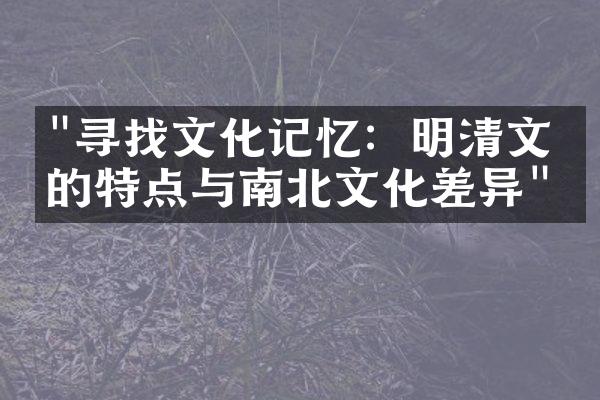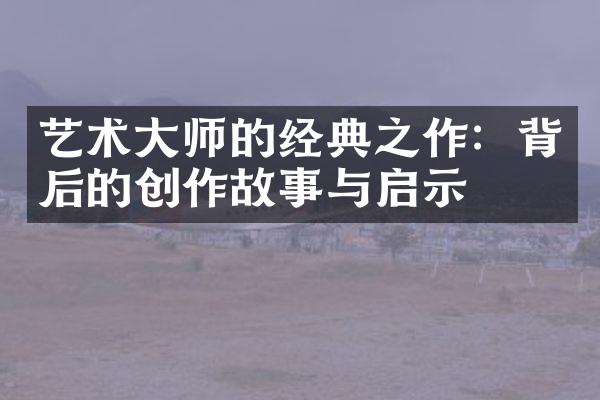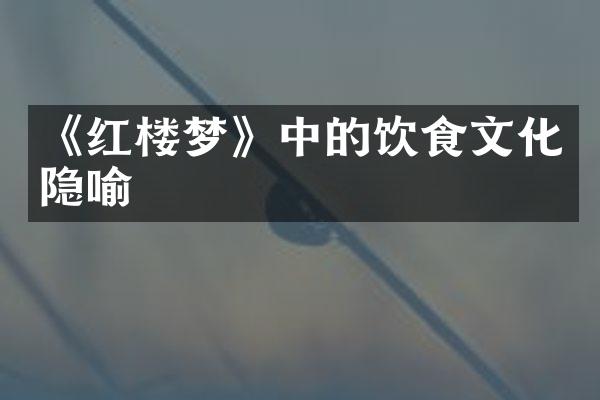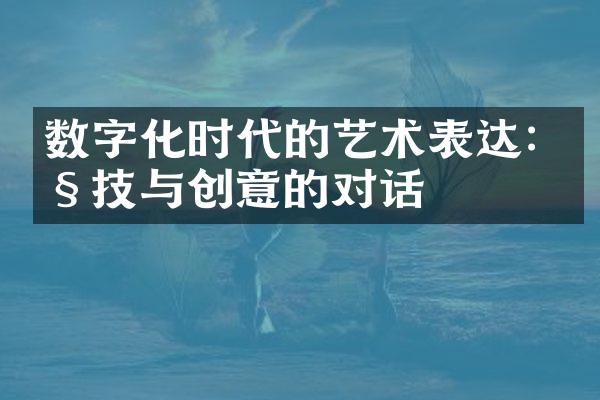从宋词到现代散文,文学语言的演变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嬗变与时代精神的转换,这一过程涉及形式突破、情感表达、语言策略等多维度的重构。以下从五个层面展开分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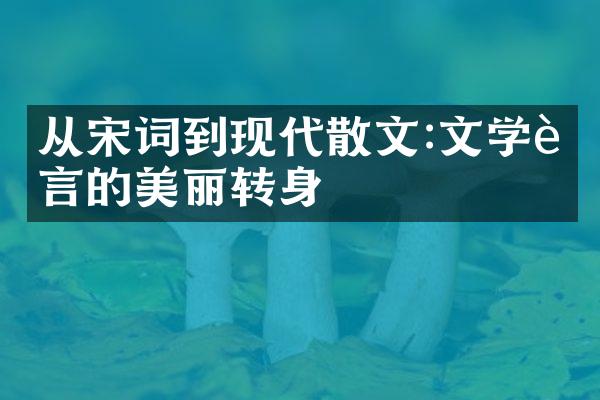
一、格律解构与自由表达
宋词依词牌填词,受平仄、押韵的严格约束,如周邦彦《兰陵王》"柳阴直,烟里丝丝弄碧"体现音韵的精密对位。现代散文彻底摒弃格律框架,鲁迅《秋夜》开篇"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",通过非韵律化的重复句式构建象征空间。这种解放使文学从音乐性转向思想性表达。
二、意象系统的现代化转型
宋词意象多依托古典审美体系,晏几道"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"中的自然意象承载固定情感范式。现代散文则创造新意象群,张爱玲《金锁记》将"月光"解构为"铜钱大的红黄湿晕",传统意象被注入现代心理学隐喻。朱自清《背影》中"橘子"成为父子情感的现代物证,体现日常生活的诗学提升。
三、修辞策略的世俗化转向
宋词修辞注重典故层积与雅言传统,辛弃疾《永遇乐》连用孙权、刘裕等六处典故。现代散文采用口语化修辞,老舍《济南的冬天》用"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"的拟人口吻,钱钟书《围城》中"海水呀,你说呀"的呼告修辞,展现知识分子的戏谑智慧。
四、叙事视角的个体化觉醒
宋词多采用类型化抒情主体,李清照"此情无计可消除"仍属士大夫情感范式。现代散文确立个体叙事权威,沈从文《湘行散记》以"我"的游历解构地域神话,萧红《回忆鲁迅先生》用私人记忆重构历史人物。这种转变呼应五四时期人的发现。
五、语言本体的现代性实验
宋词语言在文言体系中臻于精美,吴文英"听风听雨过清明"体现文言凝练美学。现代散文进行白话文实验,汪曾祺融合方言与古语创造"新笔记体",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实现现代汉语的音韵再生。翻译语体(如周作人引入希腊小品文体)进一步丰富了表达可能。
文学史学者王水照指出,这一转型实质是"文学工具论"向"文学本体论"的跨越。值得注意的是,现代散文对宋词传统的扬弃并非断裂,贾平凹《商州初录》对宋词空间叙事的转化,或董桥散文中"晚明小品与维多利亚散文的杂交",证明传统仍在创造性转化中延续生命。当代网络散文呈现的"新赋格写作"现象,暗示着新一轮的文体融合可能正在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