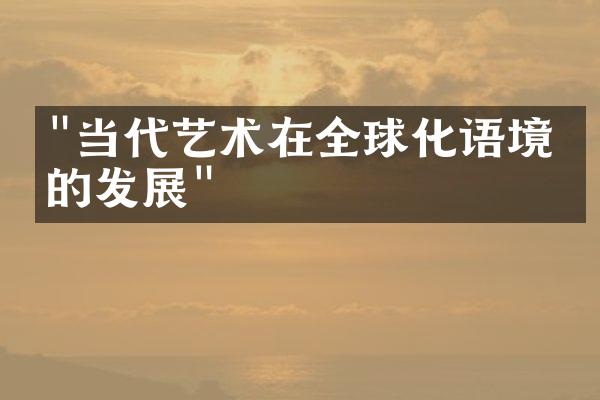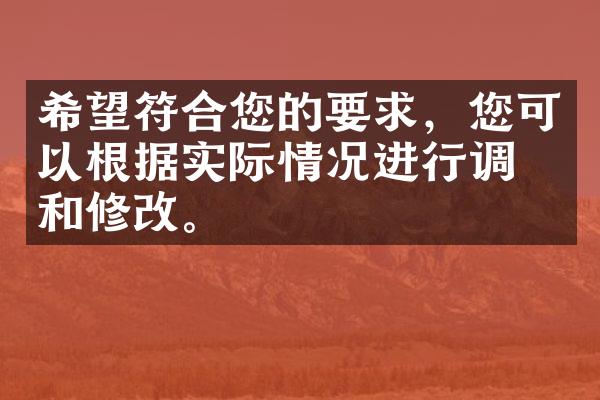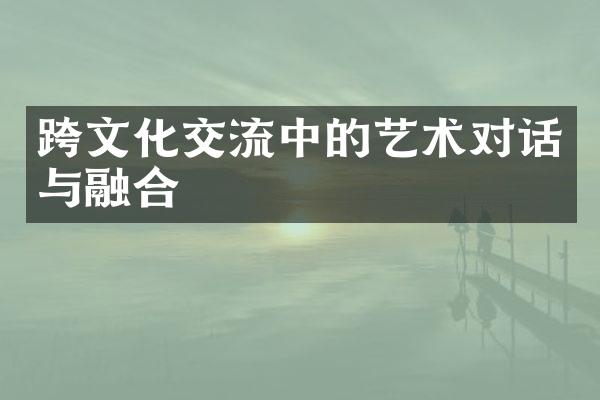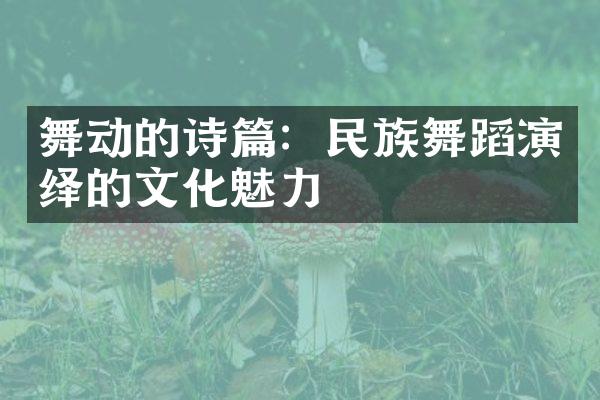音乐诗韵交响曲:穿越时光的动人旋律乐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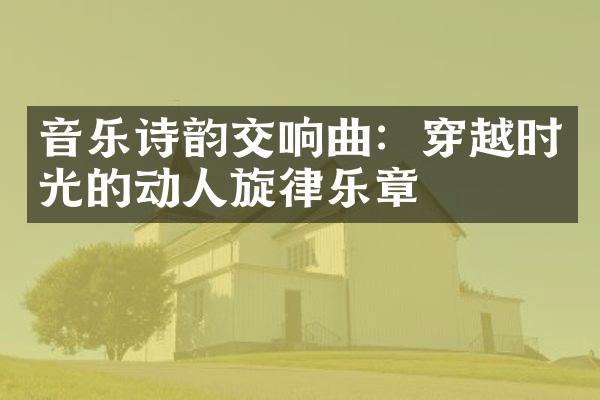
交响曲作为一种宏大的音乐形式,自18世纪古典时期以来,便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核心体裁之一。它通过多乐章的结构、丰富的配器和复杂的情感表达,构筑起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声音桥梁。以下几方面深入探讨交响曲的艺术魅力及其历史演变:
1. 结构与形式的艺术性
典型交响曲包含四个乐章:快板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奠定主题,慢板乐章展现抒情深度,小步舞曲或谐谑曲带来节奏变化,终章则以辉煌或沉思收束。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打破传统,引入人声合唱《欢乐颂》,将交响曲的叙事性和哲理性推向巅峰。
2. 管弦乐配器的色彩美学
从海顿确立的双管编制(木管、铜管、弦乐、打击乐)到马勒的千响,配器技术不断革新。柏辽兹《幻想交响曲》用英国管象征“固定乐思”,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《天方夜谭》以竖琴与独奏小提琴描绘海洋幻境,展现了音色的叙事功能。
3. 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交融
19世纪民族乐派将民间旋律融入交响曲: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糅合印第安与黑人灵歌元素,西贝柳斯《第二交响曲》以芬兰山川为灵感。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五交响曲》则用隐晦音调对抗极权,成为“苏维埃时代的音乐日记”。
4. 现代交响曲的突破与实验
20世纪后,交响曲分化出多元路径:梅西昂《图伦加利拉》引入爪佳美兰音阶和电子音效,潘德列茨基《第七交响曲“耶路撒冷”》运用微分音块拼接宗教文本。中国作曲家如谭盾在《敦煌交响曲》中结合敦煌古谱与西方结构,探索文化对话。
5. 哲学与情感的双重维度
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宗教冥想、马勒对生死议题的追问,均体现交响曲的形而上意义。而柴可夫斯基《第六交响曲“悲怆”》以凋零式结尾暗示命运无常,其情感冲击力至今未被超越。
交响曲不仅是音符的组合,更是一部流动的文明史。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规整到后现代的破碎重构,它始终在时间的裂缝中回响,成为人类精神的共振箱。每一次聆听,都是一次与百年前灵魂的隔空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