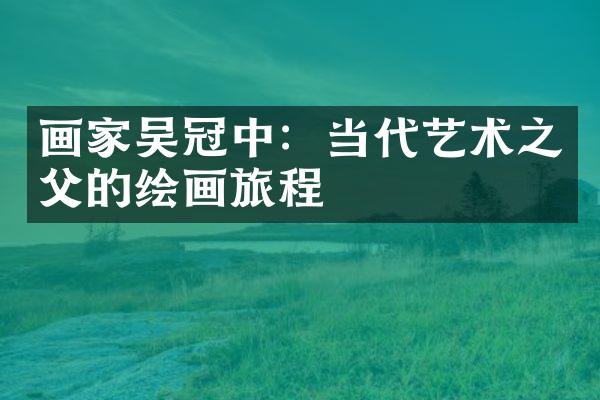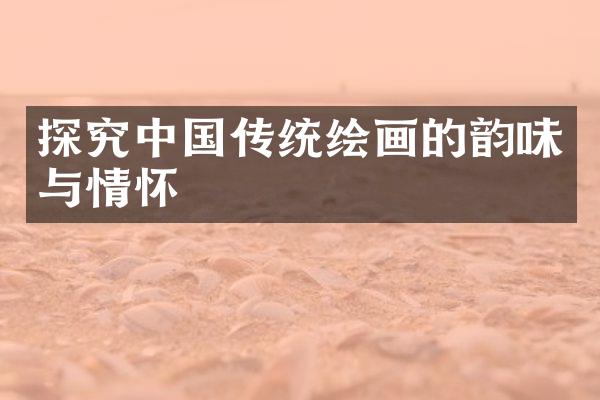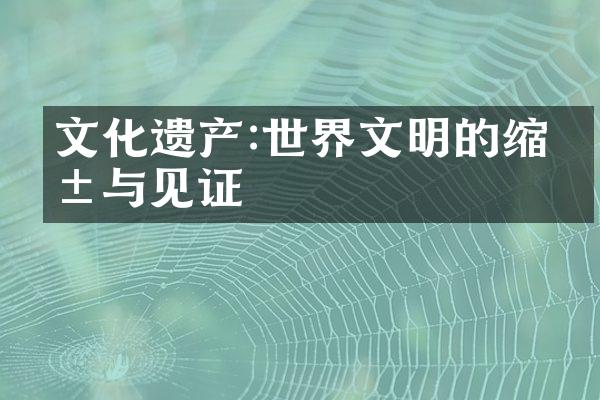潮汕木雕的南洋基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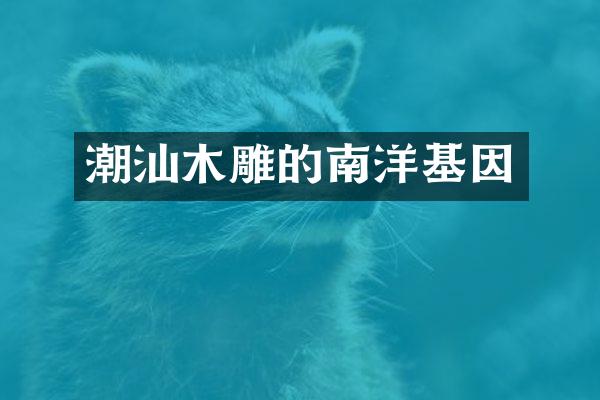
1. 题材与风格的融合
潮汕木雕在题材上吸收了许多南洋元素,如热带植物(椰树、芭蕉)、南洋动物(大象、孔雀)以及东南亚神话人物等。这些题材通过潮汕工匠的再创作,形成了独特的“南洋-潮汕”混合风格。例如,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潮汕寺庙木雕中常出现“骑象观音”“郑和下西洋”等场景,反映了南洋华侨的文化记忆。
2. 技艺的交融与创新
19世纪至20世纪初,大量潮汕工匠南下东南亚谋生,将潮汕传统的多层镂空雕刻、金漆画等技法带入南洋,同时吸收了当地马来木雕的粗犷线条和印度教雕刻的繁复纹样。例如,槟城潮州会馆的木雕构件既有潮汕的“虾蟹篓”镂空技法,又融入了马来风格的卷草纹饰。
3. 材料的跨洋流动
南洋特有的硬木(如柚木、波罗格)被潮汕工匠引入本土创作,其密度高、耐腐蚀的特性使木雕更适应湿热气候。反之,潮汕传统的樟木雕刻技法也被应用于南洋建筑,如新加坡“粤海清庙”的匾额木雕即采用潮汕“黑漆描金”工艺。
4. 宗教与民俗的互渗
潮汕木雕的宗教题材(如妈祖、大伯公)在南洋与本土信仰结合,衍生出新样式。马来西亚槟城的“广福宫”木雕神龛既保留潮汕“双凤朝牡丹”图案,又加入南洋“拿督公”神像元素,体现了信仰的本土化。
5. 商业化与跨文化传播
20世纪初,潮汕木雕作坊为迎合南洋市场需求,制作了大量“出口款”作品,如首饰盒、屏风等,纹饰上兼容中国吉祥图案与西洋花卉,这些作品通过汕头港口销往东南亚,进一步强化了艺术风格的杂交性。
潮汕木雕的南洋基因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缩影,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精细雅致,又通过南洋土壤孕育出新的生命力。这一过程展现了移民群体如何在异域环境中通过艺术重构文化认同。